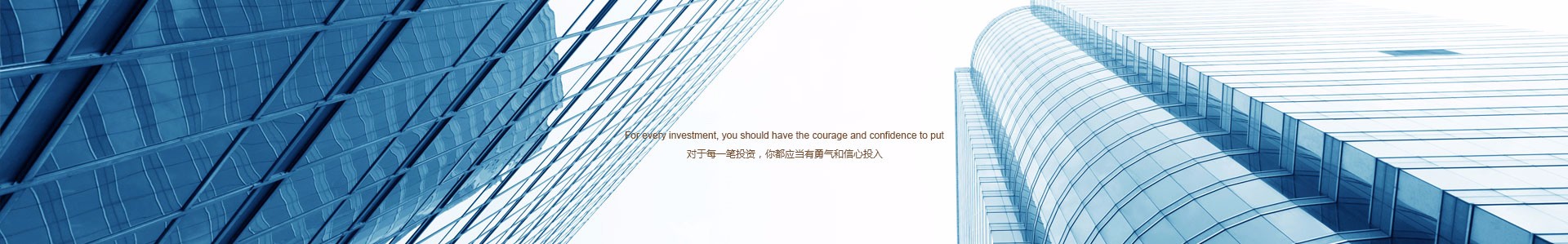竺梅先:为护佑多宝体育- 多宝体育官方网站- APP下载六百灾童 倾家荡产献生命
2025-10-21多宝体育,多宝体育官方网站,多宝体育APP下载

十月的泰清山水库,微风拂过,碧波荡漾。不远处,青灰色石亭默然矗立,名为“梅华亭”。亭柱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刻字,藏着近百年前竺梅先、徐锦华夫妇与六百个孩子的羁绊。
“当年祖父祖母创办教养院,视孩童如己出。这座亭子,是后来长大的灾童们自发所建,梅华二字,取自我祖父竺梅先与祖母徐锦华之名。”竺梅先之孙竺士性说。
自9月1日“四明丹心抗日战争中的宁波记忆”特展在宁波帮博物馆开幕后,竺梅先实业救国、庇护灾童的事迹被更多人知晓。展厅内,他名下大中银行股票、现代书局股票等展品,见证着这位甬商的经营成就。国际灾童教养院院童沈坚、戴天民1988年手绘的教养院全景图,及全体教职员的黑白老照片,则定格了竺梅先夫妇创办国际教养院的岁月。
这位宁波籍爱国实业家,既是中国近代民族造纸业的先驱,更是六百个灾童的“父亲”。
为配合特展,宁波帮博物馆推出“宁波人与抗战”主题讲座。竺士性受邀首讲,以“民族危难之际,他养育了六百个灾童”为题,讲述祖父竺梅先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动人故事。
1889年,竺梅先出生于浙江奉化长寿乡后竺村(今属萧王庙街道)。1901年,13岁的他去上海当学徒。白天他擦柜台、扛货箱、刷马桶、洗衣、生炉,晚上则用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读夜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毅然加入同盟会,投身光复上海之役,用热血践行少年之志。
战火淬炼出他“实业兴邦”的信念。1929年,竺梅先先后购得嘉兴民丰造纸厂和杭州华丰造纸厂,并亲手写下“国步维艰,端赖自强不息;民生凋敝,务须努力生产”。为打破外资对造纸业的垄断,他以发展理念治理企业,培养和集聚人才,引进先进设备与技术,创制国产新品,成为近代民族造纸业的先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毅然停下发展实业的脚步,将抗日救国作为第一要务,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带头捐献巨款,创办红十字会第十七救护医院,救治负伤将士上千人。
同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大批孤儿流落街头,他们骨瘦如柴,穿着破烂不堪,光着脚在寒风中乞讨。据统计,当时在上海租界的难童有数万人。
目睹灾童惨状,竺梅先彻夜难眠。当得知日寇正从东北、华北沦陷区掳走少儿进行奴化教育,他更意识到拯救灾童的紧迫,立下“匹夫虽微,兴亡有责,绵力所及,倾倒不辞”的誓言,毅然决定要救助这些孩子。
1938年4月,竺梅先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执委会上疾呼,“国家灾难深重,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发起创办灾童教养院的倡议,随即展开筹备工作,最终将教养院选址在奉化忠义乡(今属奉化莼湖街道)废弃的泰清寺。7月15日,国际灾童教养院在上海正式成立,由竺梅先任院长,夫人徐锦华任副院长。
“教养院无外国师生,亦无国际捐款。取名国际并聘请8位外国人担任挂名院董,是为了应付日伪军及土匪。选址泰清寺,也是因为那里地处深山,隐蔽且安全。且寺院面积大,能容纳数百名孩子。”竺士性解释。
1938年8月31日,第一批389名灾童整装齐赴泰清寺,竺梅先神情庄重地叮嘱“毋忘国仇家恨,应发奋自强,努力学习,强健身体,将来要为国家牺牲奉献。”这句话,犹如灯塔般指引着这些孩子们今后的人生。
荒废的泰清寺,断壁爬满蛛网,石阶覆着厚尘,却因竺梅先夫妇与数百灾童的到来,重焕生机。他们一砖一瓦修缮扩建,一梁一柱加固,将昔日的大殿改成大礼堂、南大门前辟成球场、寺前的琅溪修成游泳池最让人动容的是院墙的改变,竺梅先在院墙题写上“卧薪尝胆,明耻教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6个字,这既是他对孩子们的期许,也是对民族未来的信念。
两位院长则住在寺院后山坡的三间草屋,取名“岁寒草堂”,取《论语》“岁寒知松柏”之意。草屋是孩子们最爱的去处,许多孩子都住过,在孩子们心中,岁寒草堂是温暖的,是亲切的,更是神圣的。深夜,徐锦华总提着油灯巡寝室,见孩子踢被就轻轻掖好,听孩子咳嗽便端来热姜汤。在孩子们的心中,两位院长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
教养院奉行“教养兼施,德智体技并重”的理念。既设有语文、数学等文化课,也有纺织、木工、烹饪等技能课,甚至开设了英语课。“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教育观念相当领先。”竺士性说。《满江红》《正气歌》是教养院必背篇目,两位院长常亲自授课,教孩子们在“时穷节乃见”的字句里知晓担当。
教养院还有自己的院歌,今年99岁的院童戴天民依然清楚记得并动情吟唱:“吾生多幸,值风潮鼓荡,卷入洪炉百炼千锤成铁汉家山虽破,有黄农裔胄,五族同胞一德齐心修学业少康一旅,中兴责在吾曹。”句句寄予着竺梅先对广大院童的殷切期望。
教养院收容人数最多时,有六百多名院童,最小的仅四岁,最大的十五岁。再加上70多名教职人员,近700名师生员工每天粮食就需要五六百斤。
面对如此巨大的开支,竺梅先开始四处筹集经费。据竺士性编著的《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史料集》(内收《历年捐款清册》)记载,从1938年7月收到第一笔捐款至1940年12月最后一笔捐款,教养院共收到捐款332笔,总计35万元(其中个人和团体捐款12万余元、竺梅先夫妇在这期间捐出13万余元)。
1940年,浙东遭遇粮荒,教养院的米缸见了底。竺梅先被推选为鄞县粮食调剂委员会主任,他辗转从浙南购得15万石粮食,冒着生命危险运送回宁波,以救当地百姓和教养院之难。
自1941年起,宁波地区沦陷,局势恶化,教养院没有再收到任何捐款,重担彻底压在竺梅先一人肩上。他没有犹豫,转身将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民丰、华丰造纸厂抵押出去,又忍痛变卖宁绍轮船公司的股票。
据史料记载,教养院五年内总投入约100万元,竺梅先付出了近80万元。他“实业救国”攒下的家底,全化作了孩子们碗里的稀粥、手中的课本,真正践行了“其实毁家不惜,早矢沉舟破釜之忱”。
由于筹粮途中连续长途跋涉,风餐露宿,1942年春,竺梅先在赴金华永康为教养院购粮返回途中不幸倒下。5月30日,他因病逝世,年仅54岁。弥留之际,他依然念念不忘全体院童,反复叮嘱徐锦华:“一定要把孩子们好好抚养,直到他们能自立。”当其灵柩运抵泰清寺时,山路上跪满了教养院的学生和当地的百姓,山谷中回荡着悲恸的哭声,久久未能散去。
竺梅先逝世后,教养院的经费、物资更加困难,徐锦华咬牙担下重任,正如她所说“用我们的血来浇灌民族的嫩芽”。她苦撑到1943年,直到将每个孩子都妥善安置,才不舍地锁上了教养院的大门。后来,她来到嘉兴民丰造纸厂职工子弟小学任教,将对丈夫的深切思念、对六百灾童的牵挂融入到教书育人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守护与传承。
“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当年的灾童,听他们讲教养院的故事,讲后来的人生。”竺士性动情地说。
昔日院童历经人生磨砺,未负竺梅先“下之使其立身,上之乃能报国”的殷切期望。他们或投身抗日,或教书育人,或救死扶伤,各展其才。他们将在教养院中铸就的健康向上的思想品行与扎实学识,化为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坚实力量。
竺士性后来循着线索与当年的院童戴天民取得联系。戴天民对当年在教养院的生活始终满怀感恩。“我们兄妹几个自幼失怙,在上海又无亲人依靠,若不是竺、徐两位院长,早已不在人世了。”戴天民说。
当年,13岁的他与妹妹戴乙仙、弟弟戴天赋,还有小爷叔戴云森一同踏入教养院,这里成了他们风雨飘摇中的避风港。教养院解散后,戴天民与戴云森一同奔赴战场,加入抗日武装,戴云森不幸在上海浦东壮烈牺牲,戴天民历经九死一生。戴乙仙与小弟返回上海后,始终牵挂他们的徐锦华,还曾亲赴上海探望。在长辈的关怀下,戴天赋后来也投身革命洪流。
戴乙仙在《情深似海缅怀竺梅先、徐锦华两位院长》一文中写道:“在这世上,再找到像竺梅先、徐锦华两位院长这般慈爱的父母亲,已绝无可能,他们二老在我们兄妹心目中,比生身父母还要亲。”
竺梅先幼子竺培国,9岁时便与灾童同吃糙米饭、同盖旧棉絮,在教养院中耳濡目染父母忠国爱民、毁家纾难的担当,父亲“匹夫虽微,兴亡有责”的箴言,深深融入他血脉。1952年,为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年仅23岁的竺培国英勇牺牲,长眠在奉化烈士陵园。“六叔用生命践行了祖父的教诲,他是我们家族的骄傲。”竺士性说。
沙耆的前妻孙佩钧曾带着幼子沙天行在教养院执教。1943年教养院解散前夕,她将年幼的儿子托付给家人照料,与妹妹孙佩玉赴皖南参加抗日武装,随后转战华东。后来她任职中国人民银行,为祖国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
这份情谊更跨越海峡两岸。已故院童彭竹予(原名彭长根),去世前住在台湾云林县,曾写下《背负一世恩情为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六十周年记》。这位知名作家,为感念竺梅先的再生之恩改名竹予,曾六次专程从台湾来到教养院旧址,视教养院为自己的“生命发源地和学识基础的大烘炉”。他曾这样赞叹竺梅先:“他,只是一个商人,平凡得像你我,但你我又不及他开阔胸襟的千万分之一,原因就在他有强烈的爱国情操,从不把自己的生命、利益、名望紧握在掌股上。”
1953年,泰清山岙建起了浩渺的泰清水库,国际灾童教养院旧址静静地沉入了库底,但这份记忆从未被遗忘。1990年,昔日院童在泰清水库旁高地建造了一座纪念亭,从两位院长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命名“梅华亭”,亭前两柱子上镌刻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寄托了院童们对两位院长发自肺腑的情感。2015年,教养院史料陈列馆正式开馆,用实物与文字记录下那段岁月。2020年,系列纪录片《梅华和他们的孩子们》拍摄播出,更直观地展示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如今,这份记忆迎来更多回响。今年3月17日,在宁波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位于鄞州区五乡镇宝幢村联合老公墓的竺梅先墓被纳入历史文物保护点。于竺士性和家族后人而言,家族传承的脉络愈发清晰,指引着他们更好传承竺梅先“匹夫有责”的精神。6月,以竺梅先夫妇为原型的长篇小说《钟声》出版,让这段往事走进更多人心中。9月1日,“四明丹心抗日战争中的宁波记忆”特展开展,展出了与竺梅先相关的展品,更让这段往事有了鲜活具象的依托。
竺士性则是这段记忆坚定的守护者与传承者。自退休后,他便专注搜集祖父竺梅先及家族英烈的历史资料,走访旧址、拜访当年的院童。2018年,他出版《匹夫虽微,兴亡有责竺梅先传》,如今该书仍在重写修订,只为修正谬误、补充新篇。拜访当年院童时,年过九十的周世良将一沓教养院旧照郑重托付给他。此外,对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院童们的次次探访,积攒下沉甸甸的回忆与殷切的嘱托,竺士性意识到,必须更为全面、真实地记载教养院的故事。2022年,他编著了《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史料集》,让那段岁月更加清晰可见。
竺梅先在民族危亡之际将个人命运与六百灾童、民族未来相连,他不仅为怜悯灾童而施救,还寓有培扶国脉的重大意义。他的选择,不仅彰显了个人的责任和担当,更彰显了宁波商帮“心怀天下”的精神,在危难时以个人财富护民族未来,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至今仍激励着后人勇担使命。
如今,国际灾童教养院的旧址虽沉于水底,但山间的“梅华亭”依旧屹立。竺梅先夫妇用生命托举的六百个生命,早已长成支撑家国的栋梁。他们在民族危难时的选择,是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最响亮、最动人的回答。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312017004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1104076
十月的泰清山水库,微风拂过,碧波荡漾。不远处,青灰色石亭默然矗立,名为“梅华亭”。亭柱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刻字,藏着近百年前竺梅先、徐锦华夫妇与六百个孩子的羁绊。
“当年祖父祖母创办教养院,视孩童如己出。这座亭子,是后来长大的灾童们自发所建,梅华二字,取自我祖父竺梅先与祖母徐锦华之名。”竺梅先之孙竺士性说。
自9月1日“四明丹心抗日战争中的宁波记忆”特展在宁波帮博物馆开幕后,竺梅先实业救国、庇护灾童的事迹被更多人知晓。展厅内,他名下大中银行股票、现代书局股票等展品,见证着这位甬商的经营成就。国际灾童教养院院童沈坚、戴天民1988年手绘的教养院全景图,及全体教职员的黑白老照片,则定格了竺梅先夫妇创办国际教养院的岁月。
这位宁波籍爱国实业家,既是中国近代民族造纸业的先驱,更是六百个灾童的“父亲”。
为配合特展,宁波帮博物馆推出“宁波人与抗战”主题讲座。竺士性受邀首讲,以“民族危难之际,他养育了六百个灾童”为题,讲述祖父竺梅先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动人故事。
1889年,竺梅先出生于浙江奉化长寿乡后竺村(今属萧王庙街道)。1901年,13岁的他去上海当学徒。白天他擦柜台、扛货箱、刷马桶、洗衣、生炉,晚上则用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读夜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毅然加入同盟会,投身光复上海之役,用热血践行少年之志。
战火淬炼出他“实业兴邦”的信念。1929年,竺梅先先后购得嘉兴民丰造纸厂和杭州华丰造纸厂,并亲手写下“国步维艰,端赖自强不息;民生凋敝,务须努力生产”。为打破外资对造纸业的垄断,他以发展理念治理企业,培养和集聚人才,引进先进设备与技术,创制国产新品,成为近代民族造纸业的先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毅然停下发展实业的脚步,将抗日救国作为第一要务,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带头捐献巨款,创办红十字会第十七救护医院,救治负伤将士上千人。
同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大批孤儿流落街头,他们骨瘦如柴,穿着破烂不堪,光着脚在寒风中乞讨。据统计,当时在上海租界的难童有数万人。
目睹灾童惨状,竺梅先彻夜难眠。当得知日寇正从东北、华北沦陷区掳走少儿进行奴化教育,他更意识到拯救灾童的紧迫,立下“匹夫虽微,兴亡有责,绵力所及,倾倒不辞”的誓言,毅然决定要救助这些孩子。
1938年4月,竺梅先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执委会上疾呼,“国家灾难深重,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发起创办灾童教养院的倡议,随即展开筹备工作,最终将教养院选址在奉化忠义乡(今属奉化莼湖街道)废弃的泰清寺。7月15日,国际灾童教养院在上海正式成立,由竺梅先任院长,夫人徐锦华任副院长。
“教养院无外国师生,亦无国际捐款。取名国际并聘请8位外国人担任挂名院董,是为了应付日伪军及土匪。选址泰清寺,也是因为那里地处深山,隐蔽且安全。且寺院面积大,能容纳数百名孩子。”竺士性解释。
1938年8月31日,第一批389名灾童整装齐赴泰清寺,竺梅先神情庄重地叮嘱“毋忘国仇家恨,应发奋自强,努力学习,强健身体,将来要为国家牺牲奉献。”这句话,犹如灯塔般指引着这些孩子们今后的人生。
荒废的泰清寺,断壁爬满蛛网,石阶覆着厚尘,却因竺梅先夫妇与数百灾童的到来,重焕生机。他们一砖一瓦修缮扩建,一梁一柱加固,将昔日的大殿改成大礼堂、南大门前辟成球场、寺前的琅溪修成游泳池最让人动容的是院墙的改变,竺梅先在院墙题写上“卧薪尝胆,明耻教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6个字,这既是他对孩子们的期许,也是对民族未来的信念。
两位院长则住在寺院后山坡的三间草屋,取名“岁寒草堂”,取《论语》“岁寒知松柏”之意。草屋是孩子们最爱的去处,许多孩子都住过,在孩子们心中,岁寒草堂是温暖的,是亲切的,更是神圣的。深夜,徐锦华总提着油灯巡寝室,见孩子踢被就轻轻掖好,听孩子咳嗽便端来热姜汤。在孩子们的心中,两位院长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
教养院奉行“教养兼施,德智体技并重”的理念。既设有语文、数学等文化课,也有纺织、木工、烹饪等技能课,甚至开设了英语课。“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教育观念相当领先。”竺士性说。《满江红》《正气歌》是教养院必背篇目,两位院长常亲自授课,教孩子们在“时穷节乃见”的字句里知晓担当。
教养院还有自己的院歌,今年99岁的院童戴天民依然清楚记得并动情吟唱:“吾生多幸,值风潮鼓荡,卷入洪炉百炼千锤成铁汉家山虽破,有黄农裔胄,五族同胞一德齐心修学业少康一旅,中兴责在吾曹。”句句寄予着竺梅先对广大院童的殷切期望。
教养院收容人数最多时,有六百多名院童,最小的仅四岁,最大的十五岁。再加上70多名教职人员,近700名师生员工每天粮食就需要五六百斤。
面对如此巨大的开支,竺梅先开始四处筹集经费。据竺士性编著的《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史料集》(内收《历年捐款清册》)记载,从1938年7月收到第一笔捐款至1940年12月最后一笔捐款,教养院共收到捐款332笔,总计35万元(其中个人和团体捐款12万余元、竺梅先夫妇在这期间捐出13万余元)。
1940年,浙东遭遇粮荒,教养院的米缸见了底。竺梅先被推选为鄞县粮食调剂委员会主任,他辗转从浙南购得15万石粮食,冒着生命危险运送回宁波,以救当地百姓和教养院之难。
自1941年起,宁波地区沦陷,局势恶化,教养院没有再收到任何捐款,重担彻底压在竺梅先一人肩上。他没有犹豫,转身将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民丰、华丰造纸厂抵押出去,又忍痛变卖宁绍轮船公司的股票。
据史料记载,教养院五年内总投入约100万元,竺梅先付出了近80万元。他“实业救国”攒下的家底,全化作了孩子们碗里的稀粥、手中的课本,真正践行了“其实毁家不惜,早矢沉舟破釜之忱”。
由于筹粮途中连续长途跋涉,风餐露宿,1942年春,竺梅先在赴金华永康为教养院购粮返回途中不幸倒下。5月30日,他因病逝世,年仅54岁。弥留之际,他依然念念不忘全体院童,反复叮嘱徐锦华:“一定要把孩子们好好抚养,直到他们能自立。”当其灵柩运抵泰清寺时,山路上跪满了教养院的学生和当地的百姓,山谷中回荡着悲恸的哭声,久久未能散去。
竺梅先逝世后,教养院的经费、物资更加困难,徐锦华咬牙担下重任,正如她所说“用我们的血来浇灌民族的嫩芽”。她苦撑到1943年,直到将每个孩子都妥善安置,才不舍地锁上了教养院的大门。后来,她来到嘉兴民丰造纸厂职工子弟小学任教,将对丈夫的深切思念、对六百灾童的牵挂融入到教书育人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守护与传承。
“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当年的灾童,听他们讲教养院的故事,讲后来的人生。”竺士性动情地说。
昔日院童历经人生磨砺,未负竺梅先“下之使其立身,上之乃能报国”的殷切期望。他们或投身抗日,或教书育人,或救死扶伤,各展其才。他们将在教养院中铸就的健康向上的思想品行与扎实学识,化为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坚实力量。
竺士性后来循着线索与当年的院童戴天民取得联系。戴天民对当年在教养院的生活始终满怀感恩。“我们兄妹几个自幼失怙,在上海又无亲人依靠,若不是竺、徐两位院长,早已不在人世了。”戴天民说。
当年,13岁的他与妹妹戴乙仙、弟弟戴天赋,还有小爷叔戴云森一同踏入教养院,这里成了他们风雨飘摇中的避风港。教养院解散后,戴天民与戴云森一同奔赴战场,加入抗日武装,戴云森不幸在上海浦东壮烈牺牲,戴天民历经九死一生。戴乙仙与小弟返回上海后,始终牵挂他们的徐锦华,还曾亲赴上海探望。在长辈的关怀下,戴天赋后来也投身革命洪流。
戴乙仙在《情深似海缅怀竺梅先、徐锦华两位院长》一文中写道:“在这世上,再找到像竺梅先、徐锦华两位院长这般慈爱的父母亲,已绝无可能,他们二老在我们兄妹心目中,比生身父母还要亲。”
竺梅先幼子竺培国,9岁时便与灾童同吃糙米饭、同盖旧棉絮,在教养院中耳濡目染父母忠国爱民、毁家纾难的担当,父亲“匹夫虽微,兴亡有责”的箴言,深深融入他血脉。1952年,为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年仅23岁的竺培国英勇牺牲,长眠在奉化烈士陵园。“六叔用生命践行了祖父的教诲,他是我们家族的骄傲。”竺士性说。
沙耆的前妻孙佩钧曾带着幼子沙天行在教养院执教。1943年教养院解散前夕,她将年幼的儿子托付给家人照料,与妹妹孙佩玉赴皖南参加抗日武装,随后转战华东。后来她任职中国人民银行,为祖国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
这份情谊更跨越海峡两岸。已故院童彭竹予(原名彭长根),去世前住在台湾云林县,曾写下《背负一世恩情为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六十周年记》。这位知名作家,为感念竺梅先的再生之恩改名竹予,曾六次专程从台湾来到教养院旧址,视教养院为自己的“生命发源地和学识基础的大烘炉”。他曾这样赞叹竺梅先:“他,只是一个商人,平凡得像你我,但你我又不及他开阔胸襟的千万分之一,原因就在他有强烈的爱国情操,从不把自己的生命、利益、名望紧握在掌股上。”
1953年,泰清山岙建起了浩渺的泰清水库,国际灾童教养院旧址静静地沉入了库底,但这份记忆从未被遗忘。1990年,昔日院童在泰清水库旁高地建造了一座纪念亭,从两位院长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命名“梅华亭”,亭前两柱子上镌刻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寄托了院童们对两位院长发自肺腑的情感。2015年,教养院史料陈列馆正式开馆,用实物与文字记录下那段岁月。2020年,系列纪录片《梅华和他们的孩子们》拍摄播出,更直观地展示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如今,这份记忆迎来更多回响。今年3月17日,在宁波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位于鄞州区五乡镇宝幢村联合老公墓的竺梅先墓被纳入历史文物保护点。于竺士性和家族后人而言,家族传承的脉络愈发清晰,指引着他们更好传承竺梅先“匹夫有责”的精神。6月,以竺梅先夫妇为原型的长篇小说《钟声》出版,让这段往事走进更多人心中。9月1日,“四明丹心抗日战争中的宁波记忆”特展开展,展出了与竺梅先相关的展品,更让这段往事有了鲜活具象的依托。
竺士性则是这段记忆坚定的守护者与传承者。自退休后,他便专注搜集祖父竺梅先及家族英烈的历史资料,走访旧址、拜访当年的院童。2018年,他出版《匹夫虽微,兴亡有责竺梅先传》,如今该书仍在重写修订,只为修正谬误、补充新篇。拜访当年院童时,年过九十的周世良将一沓教养院旧照郑重托付给他。此外,对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院童们的次次探访,积攒下沉甸甸的回忆与殷切的嘱托,竺士性意识到,必须更为全面、真实地记载教养院的故事。2022年,他编著了《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史料集》,让那段岁月更加清晰可见。
竺梅先在民族危亡之际将个人命运与六百灾童、民族未来相连,他不仅为怜悯灾童而施救,还寓有培扶国脉的重大意义。他的选择,不仅彰显了个人的责任和担当,更彰显了宁波商帮“心怀天下”的精神,在危难时以个人财富护民族未来,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至今仍激励着后人勇担使命。
如今,国际灾童教养院的旧址虽沉于水底,但山间的“梅华亭”依旧屹立。竺梅先夫妇用生命托举的六百个生命,早已长成支撑家国的栋梁。他们在民族危难时的选择,是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最响亮、最动人的回答。